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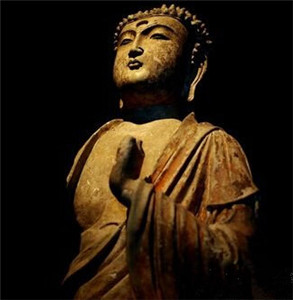
八月初旬,陈真如、黄忏华、潘怀素、张剑峰等诸居士不约而同集缙云山。至八日、大雨滂沱,暑气顿消。太虚大师以时机难得,于此新凉之际,在大讲堂召开一佛法座谈会。出席者,前述四人及陶冶公、金觉范、龚星楼、卫立民诸居士,暨萧、原二君,并有印顺、苇舫、尘空、妙钦、正果、开一诸法师等。而本院全体员生,亦列席旁听。由大师亲临主席,先提出“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”一问题,请出席人藉此作为论端,发表意见。仅陈真如、潘怀素二居士与印顺法师三人发言,已逾三时有余。大师竟因历时过久,勉及尽辞而致病。
太虚 “秋风秋雨送新凉”!陈真如居士等,都是游于华严法界中的善知识,在这时期,不约而同地俱集本山,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缘会,本院(汉藏教理院)略备粗陋茶点,召开这个座谈会,在以法相资,同得法喜。
我先提出问题,作为论端,那就是“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”。庄子天下篇中评论当时学说思想说:“各得道之一察,欲以易天下”。所谓易天下,就是改善现实社会。尤其现时的学说思想,大都是集中于“怎样改善现实社会”这个问题,其原因有二:一、因为现实社会的矛盾现象太多,由这矛盾的现象而产生无限的痛苦,尤其是在残杀的战争时期。所谓现实社会,即是指现在实际有组织的人类社会,人类的社会既发生了痛苦,只要是有思想、有良心的人,无不力求改进。二、由于近来各种学说的进步,社会的痛苦的确有解决的可能,因此有思想的人,不逃避现实,不脱离社会,而以全力集中急求改进。现实人类社会的痛苦,不是天然的,或什么神赐予的,而是人类自己起心不良,自相争杀而造成的。改造这种痛苦的现实社会的学说思想,现在一共有四种:一、强调民族至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国粹主义,如德国、日本是。二、民主主义,如英、美是。三、共产的社会主义,如苏联是。四、综合三种思想而改良的三民主义,如我们中国是。第一种主义将要失败,第二种民主主义的力量在全民参政,第三种的力量在劳工专政,第四种则在发展人类求生存的力量。这三种主义,当然继续推行下去,均利用科学以改进人类现实的社会为目的。
然而佛法是否也可以改造现实社会呢?佛法的存在,是否为人类所需要?如果佛法不能改造社会,不为人类所需要,那就可以不谈。假使能改造,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几种足以改进的主义,那不是不需要佛法了吗?
再深一层讲,我们应当要明白什么是佛法?什么是现实社会,以佛法的眼光看来,现实社会应当逃避吗?还是应当改进呢?或根本加以否定,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社会。从这几方面,都可以佛法观察。但今天座谈会的题目,主要的在是否可以改进现社会。
讲到这里,我连带地记起十六年前,真如居士在杭州灵隐寺和我晤面时,曾问我“佛法是否也讲救世,佛法可否救世”?我当时简单的答覆是“也讲救世,同时也可以救世”。不过“世间”的范围很广,现在的着重点,是现实的人类社会。前两年、王恩洋居士来山,我们也曾召集过一次座谈会,讨论“佛法对于战后的人类有何贡献”?他说:“佛法如眉目,可以庄严人类及明导人类”。当时有人批评它说得太过分,因为其他的宗教学说并不是盲目;但也有人说它说得不够,因为佛法并不如眉目只是人类的庄严和明见而已,应该是人类的全体大用。今天讨论的也略有相近,现在请各位对此问题发表高见!
陈真如 刚才大师提出“佛法是否可以改善现实社会”这个问题,本人觉得非常扼要。听了大师的这番伟论,使我发生很多的感想。但座谈会的时间短促,大家都要发表意见,我不能将我所感想到的尽量地说出来,只能说一个大概。
佛法对于世间,的确很重要!我们佛教徒生存在这现实的世间,不能脱离这现实的人类社会,因此与这现实的人类发生密切的关系。这不但佛教徒是如此,无论何种宗教徒也是这样。佛教对于世界人类的影响之大,尤以中国为最,但在新时代的今天,我们应当振兴使它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才好!因此大师提出这个问题。不过、我觉得佛教徒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,尤其是出家的僧众。
佛法本以出世为鹄的,因此有僧伽制度和组织。此制度和组织,有的已衰败而不适应时代了,这大师老早就已看到,并提倡改革。不过此制度所欲达到的目的在出世,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!至于制度,能够改革,固然很好,如果不能,那末、旧的制度无论如何是应该保存的。向来一班人以为和尚只是吃国家的饭,是消极厌世的社会分利份子,这我们可以置之不理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是宗教徒,无论那一个国家和民族,都是需要宗教的。佛教既是伟大的宗教之一,决不是一句话可以抹煞其价值的。但僧伽的堕落和寺庙内部的腐败,这也是事实,我们应当承认。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,人民的生活习惯所受的佛教的影响,比儒家还要大。如某些青年,他尽管不信佛,待他的家里一有什么事,其家长必到寺院打斋供僧或念佛做佛事等,其影响之大,可见一斑。总之、佛法以出世为鹄的,有佛法因有僧众,有寺庙,有制度,有教育;而僧众的责任,则为继续如来的慧命。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,坚持自己的立场,决不可因人家讥谤而摇动。
佛法与现实世间,在兄弟一向的见解,以为社会的政治、经济等问题,不是佛法正面,而是旁面的。这就是说,佛教徒不应从事正面的政治、经济等活动。因若从事正面的活动,无论在形式上和作用上,均为佛法的力量所不及。在历史上,佛法一向为帝王所尊重,以之而感化世间改善世间的亦未尝不有,但其正面所作的事,皆为世间的事,如菩萨现宰官身以法律为正面,现将军身以带兵与军令等为正面,他们绝对不能是僧侣。如果它有佛法的修养,内含菩萨心肠,与敌人短兵相接,对敌方的投降份子,它就不会杀,否则他就违反了菩萨心。现将军身带兵与敌短兵相接是正面的世间事,对敌方投诚的份子不杀害,则为旁面的佛法。认清了这点,方可以说是认清了现实世间。
若佛法专以从事政治、经济活动而治世,恐怕早已无佛法存在了。中国在五胡乱华的时候,符坚派人迎鸠摩罗什来中国宏法,但因乱战撕杀,罗什停留凉州而不能来。待姚兴遣兵迎罗什到长安,而符坚的国早亡。这是表示佛法是超时空性的,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,并不如欧洲的宗教,可以被人利用为政治等侵略工具的。所以即是我们做了政治家或经济家,对正面的世间事应当尽职,而佛法只能从旁助理,这是应当认清楚的!
还有一点意见,那就是我们佛弟子明了佛法,应如何修菩萨行。这是一个根本问题。这就是说,无论是出家也好,工、商各界也好,在复杂的现实社会当中,我们应该有什么不同的表现?以佛弟子的立场,在繁杂多样性的众生当中,如果有特别的表现,这种表现,比什么力量都大!行菩萨道,我以为只是“悲智”二字,我们应当随时记着!“悲”、就是伟大的同情,无条件的忘自我而为他人,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。如世间有些痛苦,不是由有情自己本身发生的,而是由团体中间发生的,这种痛苦,世人无法解决,唯有发大悲心的菩萨才能解决。此种伟人,实为其他宗教所不及!经里说:从前有一个人,欲纂王位,他喜于射箭,可以射中空中的飞鸟;当他放箭射王时,那箭在国王的面前忽然堕了地。原来那国王是菩萨,他看见对方的箭射来了,即入慈心三昧,因此箭就堕了地。射手见了这种现象,极为恐怖,预备再射第二箭。国王连声道:“你如果再射,就会射到你自己”。射手听了他的话,大受感化。由此故事,可以证明旁面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们如果以佛法到社会上去从事正面的经济、政治等,就要失掉自己的立场,结果是同流合污。“智”、就是智慧,要有智慧,才可以认识世间的一切,见世间如幻如化,因争的撕杀而起怜悯而发生大悲,所以悲智是同一根源的。佛法对众生的利益,则是救众生的慧命!时间多了,余待下次再说。
潘怀素 大师提出这个问题,意思就是说:社会已经有了毛病,须要改善,如世界大战即为毛病的表现。这种毛病,科学是否能改善呢?
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,就是因为有生命,有生命就要生活,为了要生活,不能不随时为生活而奔驰,就是临死的时候它也要挣扎。现在社会的一切,都是向上发展的:茅屋可以遮风雨,大洋房也是遮风雨,但大洋房比茅屋好些。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,就是因为人类要好的生活。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由于人类自私观念的原故,所以社会发生斗争。在原始社会里,生活取于自然;到了贵族社会,以为生活资养由于天赐;而现在则以为是由于人类自己的争取,因此不得不斗争。如我们这里许多人,若只有一杯茶,但因各人实际的须要,就不能不发生争夺。由于这个原故,于是乎就有你的、我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等等不同的观念。又如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,强调日耳曼民族至上,以科学的眼光看来,都是极端错误的。如果将这些错误观念改正,那末社会也就可以改好。但“好”以什么为标准呢?我以为应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。这个标准,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。若只就个人主观的玄想以为就是好的,那结果就会因各人的见解不同而发生纷争。如我们所吃的米,本是大家的力量做出来的,那末就应共同享受,在这中间不应有什么特殊的阶级存在。以此种标准去衡量社会,才是真正的衡量。因此改造社会,应当从大众着眼。但众生无量,个性不同,现在要做到这步,事实是不可能。
有人以为科学发达不好,把人类的自相残杀的罪恶,一概归罪于科学,这是不懂科学!因为科学的本身是无我的,无罪的;科学的好坏,只看人类自己利用得当与否!如花生可以吃,但吃多了,也可以胀死人。
人类的历史,往往在错误的观念中兜圈子,如果这错误的观念不改变,社会就无法改善。我们知道,生命是无上宝贵的东西,然而生命的本源,科学却无法解释。如生物学分析到最后,对于生物的本源,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概念。生命无穷,故每个生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同,而维持这宝贵生命的存在,就需要资料的充足。
更向上一点,我们的生活要好,但好的标准都由于各个人的主观不同。如穷人茅房也好,阔人则要大洋房才好。尽管他们的好有区别,但都由于他们自己的感觉。这种感觉,就是所谓判断力。因各人的主观不同,故他们的判断力也就有异,以主观的立场去衡量社会,这是错误的,但这种错误,科学却无法改变。
再看──西洋的──宗教,是否可以改进社会呢?也不可能。西洋的宗教与中国的宗教,其内容根本不同。西洋的宗教,以为宇宙万有均由神所造,中世纪的几百年,就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。基督教的初创,其目的本亦在为改进人类社会,但结果被人利用作为政治的工具,因此造成中世纪的黑暗时期。自文艺复兴、科学发达以后,欧洲根本就没有几个真实信仰宗教的人。所以我说以宗教改进社会是不可能的。此外如回教、婆罗门教等,同为幼稚可笑!
科学、宗教既都不能改进社会,那末佛教呢?这我们可以从佛陀的本身来看。在佛世,当时的印度社会环境,的确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。他考察生命的来源,看到社会上森严的阶级制度,他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考虑,得到了结论。他以为众生都是平等的,生命的本质,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因此推论到社会也应当平等无差别才是。所以、佛法是否可以改造现实社会,就看每个人的无差别的平等心理是否可以建立?如果建立得起来,就可以改造现实社会。佛法之所以能够救世,也就在这点。
印顺 大师提出的问题,刚才听了两居士所发表的意见,我也有一点感想。佛法一面是以有情(生命物)为中心、为出发点的,所以佛法的目的,在使有情认识痛苦而求解放,因此有佛陀的出现,佛法的流传。因为佛法的本旨如此,所以佛法完全是为要改善人生。有情痛苦的发生,不出三方面:一、是由于自己(身心之间)所引起的,二、是由于社会(自他之间)所发生的;三、是由于自然环境(我物之间)给予的。佛法的宗旨,是为了要解决这些痛苦。但我与自然之间,只要有方法,了解自然物质的原理,就可控制利用而摆脱之。人人可以实验,像科学所说的。可是人类社会的自他之间,就不会这样简单。在某种环境之下,同一的社会关系、社会机构,他赞成,你却不满意。过去可以安全,现在就不能控制。从前热烈的追求他,现在却厌恶他。社会现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学的那样必然,就为了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在,故仅只科学是不足以改进社会的。社会的改善,可从适合多数人的要求,用社会组织的共同力去改善他,政治、法律等,都是为了这一点的。说到身心间的问题,只要肯自我反省,就可以知道比社会纠纷更复杂,更不容易把握。个人的性格、兴趣、嗜好、思想,要加改善,是很不容易的。一切宗教、修养,特别是佛教,侧重在这一点。从广义说,要改善现实的人类社会,与这三种都有关,也可说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以及宗教、佛法,都为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间。但如社会不良,没有合理的制度,那科学会变成贼害社会的东西。现代战争,不是受尽了科学的伤害吗!但这与科学本身无关。进一步,如人类私欲发展、人格堕落,那末任何社会制度,都难于改善社会!多少人假借民意,利用愚民!多少人利用政治、经济机构,来破坏社会的和平!所以这三者并重,而改善社会,应从根本的人格思想改善起,这是佛法的立场。而且、科学的进步,不一定是社会的合理与平安;社会的改善,不能担保你的身心安乐;佛法是从这究竟的观点出发的。
人类的社会组织的好坏,虽有各人的见解不同,但不是不能比较的。大概在国家强盛时,其政策就比较宽容,倾向大同;若受到压迫,在危亡之时,就要强调比较狭隘的国家、民族主义。社会的终极,当然是倾向大同。但真正的好坏,我认为应从人类的共同要求,而更当重视某一时空中的现实需要,从双方兼顾中去估量其价值。否则、任何制度都不能一定适合,这只是例子。
佛法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,可以约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两方面来讲: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不同,它是超越的,不是正面的去从事经济、政治等活动,它是以有生而到无生,超社会而得解脱。有人说:这是消极,但消极并不一定与世间无好处。如小乘圣者,它有伟大的精神修养,有高尚的人格,便可以影响社会。如中国的伯夷、叔齐,其精神感召后来的人也很多!然大乘佛法的思想,则完全不同,它以为生即无生,无生而不离生,故正面的去从事经济、政治等活动,并不妨害自己的清净解脱,它要从世间的正业去体验而得解脱,这种解脱叫做不思议解脱,这在华严经里说得很多。故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于社会,并不一定要站在旁面;政治、经济等在吻合佛法的思想体系下,何尝不是佛法?因为它主张世间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。不过、出家人倒不须要这样做。总之、佛法一是净化身心的声闻佛教,守住自己的岗位,不失自己的立场,从旁面去影响社会,不去从事正面的经济等活动,它深刻却不能广及。二、是以世间而达到清净解脱的大乘佛教,可以正面地去从事经济、政治等活动。出家人应以声闻佛教为立脚点,而在家佛教徒则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,正面的去从事政治、经济等活动,这政治、经济等就是佛法。
太虚 今天的座谈会,有三位发了言。第一是陈真如先生,他所讲的可分为两点:一、出家僧众以超俗的立场和人格的表现,从旁面的影响使社会改善。二、在家的佛教徒,虽亦正面地从事政治、经济等活动,对世间的责任尽职,而内面菩萨的大悲大智心,表现与一般人不同,无论从正面或旁面,皆可能使社会改进。
第二是潘怀素先生,他对社会的改造,说到有科学的、宗教的、佛法的。科学对于人类的历史差别性,无法解决;宗教又以神权思想来统治人类,以神为本,这只是人造的玄想,以之而改良社会是不可能的。最后谈到佛法,以佛法说众生无差别,人类的善的标准,应以大众的利益为对象,以生命无差别的理论,去观察众生,如幻如化,心性平等,故可以改进现实社会,同时认识生命的宝贵而应加以保护。但以什么方法去改进,潘先生没有说出来。
第三是印顺法师,它说佛法以有情为本,其利益的标准亦须以大众为对象,这颇与潘先生的意义接近。其所提出的方法,一是小乘佛法修养的精神,高尚的人格,从旁面去影响社会,使之改进,这与陈先生的意义接近。他又提出大乘菩萨的精神,如华严经中的无厌足王等,在表面上是罪恶的而其实它在改善世间,这是不可思议的大乘菩萨行,因为菩萨是以慈悲为本、方便为门,所以它说佛法更有直接改善世间的可能。
我以为出家制度是绝对必要的,但须把它整理好,使世人崇仰,再以方便为引导。同时、我觉得僧众的人数,宜精不宜多。
以众生心性平等的思想为出发点,使众生从根本的心理上改造起,因此菩萨愈多愈好,使每人都成为华严法界的善知识,人间也就成华藏世界。现在的问题,就是我们如何将佛法宣扬出去,使社会人士普遍地明了菩萨的伟大精神!(光宗记)林同济 (读记录后所提的意见)西方的冥契主义,分消极、积极两种,前者是自了汉,并不以改善社会为目的,如果社会人士受了他的慧光之感召而学为善为爱,那就是意外的收获,不是原定的目的。消极的冥契主义者,目的只有自进智慧之林,自得解脱之门。
积极的冥契主义者,是证到了“无上正觉”后,而感得这正觉中的重要成份,就包含著「爱”的精神,翼护一切的精神,于是本此精神而勇决地以先觉觉后觉,,结果便产生一种积极传教精神,设法使大家都来信其所信,都来接受他的宗教。传教的精神与自了汉的解脱有异,但也不离宗教信仰的本位,它道地是宗教家的一种分内事。
过此以往,则西方的冥契主义者,亦有不少直接参加社会、政治、军事的工作的,但这都是出于一时环境的“不得已”而仔肩“教外事”,不是以它为道地分内事的。
我以为三者可并行不背,佛教的未来,应当:
一、由一种严格的佛教院,训练有极精选──人数不必多而亦不可多 ──的悲智大士,以为佛教会中的顶峰人才团。他们要以自觉自救为最尽先的目的,必如是,然后可以维持“质精”的标准,维持佛教徒的“高度”。
二、由这精练团中,按各人的志趣,而分出专门修行者、执行传教者两种人。
三、在任何场合下,凡在教之正常或方便立场,认为“不容已”的社会、政治以至军事工作,似乎都应该振袂而起,来作短期或短期的担当,不宜拘拘于所谓自家的“岗位”。
究到底,宗教家固必须把他的经常工作,局限于狭义的宗教范围内。然广义说来,毕竟一切“人的事”都属宗教家“分内事”,关键在做事者与当事者的态度与立场必需是“宗教的”。而事之本身是否属于狭义的宗教性质,乃是次要问题。换句话说,我以为在非常场合下,宗教家可以──而亦应当──本宗教的立场,奋勇担任他所认为时势──环境──或义理上必须从权担当的“教外”性的事业,由一个经常的宗教家变为一个应权的政治家、社会工作家等……。
乞恕我一个门外汉的妄见!(见海刊二十五卷十一十二两期合刊)
- 上一篇:佛教对于将来人类之任务、种性
- 下一篇:与挪威哲学博士希尔达论佛学
- 太虚大师:学佛者第一步需要对佛与佛教有种认识
- 太虚大师:对于佛法僧三观,当有一贯宗旨
- 太虚大师:佛教的大乘和小乘有什么区别?
- 明贤法师:走偏的人间佛教:“人成即佛成”讹误半世纪
- 太虚大师:儒道不能解脱业力 离苦得乐必须学佛
- 太虚大师:学佛是为了什么 学佛在于离苦得乐
- 太虚大师:什么是心包太虚、量周沙界?
- 太虚大师:佛教徒应如何对待佛化婚礼?
- 太虚大师:太虚大师开示“所缘缘”的认识
- 太虚大师:太虚法师谈梦的意义
- 太虚大师:太虚大师论周易
- 太虚大师:凡夫俗子不明佛法,八大误会首当其冲
- 太虚大师:原子能与禅定神通
- 太虚大师:学佛初门由三法入
- 太虚大师:中国人的8种通病可以靠它改变
- 太虚大师: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
- 太虚大师:佛告诉你做人的五条根本道理
- 太虚大师:中日佛教文化的八点不同
- 太虚大师:经商与学佛的三大共性
- 太虚大师:文化守成与改革创新
- 星云大师: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;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- 正如法师:念《心经》比《大悲咒》更好吗?
- 印光大师:安士全书白话解
- 净慧大师:净慧法师《楞严经》浅译
- 星云大师:星云大师谈《心经》
- 文珠法师:妙法莲华经
- 大寂尼师:一般人在家里可以读诵《地藏经》吗?
- 仁清法师:听说诵大悲咒对鬼不好,请法师开示
- 星云大师:解读普贤菩萨十大愿王(附普贤行愿品全文)
- 圣严法师:关于灵魂与鬼的终极真相
- 梦参法师:梦参老和尚:金刚经
- 惟觉法师:修行人应做到的三大精进
- 心律法师:吃亏是福
- 梦参法师:梦参老和尚讲地藏本愿经
- 心律法师:什么人与佛有缘?
- 文珠法师:大方广佛华严经
- 星云大师:千江映月
- 虚云法师:多诵读《普门品》和《地藏经》
- 星云大师: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;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- 达摩祖师:《破相论》原文
- 永明延寿:宗镜录
- 正如法师:诵心经比大悲咒功德大吗
- 净善法师:净善法师:看风水与算命能否改变命运?
- 大安法师:无量寿经
- 未知:星云大师讲解
- 正如法师:梁皇宝忏 慈悲道场
- 明空法师:明空法师:《心经》中的般若智慧
- 印光大师:不科学的求子秘方,但是很灵验
- 星云大师:人身难得今已得,佛法难闻今已闻;此身不向今生度,更向何生度此身?
- 星云大师:朝看花开满树红,暮看花落树还空;若将花比人间事,花与人间事一同。
- 净界法师:打坐的时候该怎么念佛?
- 仁清法师:《大悲咒》的九种世间利益
- 正如法师:在家居士受五戒可以搭缦衣吗?
- 印光大师:命不好者求美好姻缘,有个简单方法
- 星云大师:人死后生命是怎样的?
- 星云大师:溪声尽是广长舌,山色无非清净身;夜来八万四千偈,他日如何举似人?
- 大安法师:大安法师讲解
- 明安法师:把握当下不后悔
- 星云大师:天为罗帐地为毡,日月星辰伴我眠;夜间不敢长伸足,恐怕踏破海底天。
- 净慧法师:净慧法师:《妙法莲华经》浅释
- 白云禅师:傲慢与偏见,学佛人要远诸傲慢,调整偏见
- 宗性法师:佛教说不能执著,是否意味着看淡甚至放弃努力理想?
- 广钦和尚:在家学佛,应如何做人?
- 弘一法师/庆裕:做真实的自己
- 慈庄法师:行脚云游是什么意思?
- 觉真法师:放下不快乐就是快乐
- 觉真法师: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
- 觉真法师:有没有办法掌握未来?
- 觉真法师:你快乐吗?有没有试过不快乐?
- 慧广法师:错了怎么办?
- 崇慈法师:修行到底是修什么?
- 慧广法师:生活感言,人生总有喜怒哀乐的
- 本源法师:至心精进,专注于目标,成功自然水到渠成
- 如瑞法师:老实念佛,重在一生坚持不懈忆佛念佛
- 明海大和尚:明海大和尚的新春勉励:一个出家人的四件事情
- 静波法师:先告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,别人才真正愿意去做
- 济群法师:弘扬佛法是每个佛弟子的责任
- 清净法师:供奉韦驮菩萨和伽蓝菩萨消除障缘
- 仁禅法师:五种适合绝大多数人修的「持名念佛」方法
- 净善法师:净善法师:看风水与算命能否改变命运?
- 如瑞法师:身外之财终舍离,所造之业如影随
- 静波法师:佛法的中道观
- 济群法师:明心见性是怎么来的?利根是天生的吗?
- 如瑞法师:佛性不分南与北,为人不与比高低,广修福慧获法喜
- 本源法师:学习佛陀冥想静坐,就可以悟道成佛吗?
- 静波法师:深着虚妄法 坚受不可舍
- 济群法师:人为什么要摆脱痛苦和烦恼,目的是什么?
- 本源法师:出家人与在家信徒要保持距离,才能更好地度化众生
- 如瑞法师:什么是不善业,为什么要远离一切不善业?
- 明海法师:当业障现前时怎么办?随缘了业,究竟解脱
- 济群法师:如何面对喜欢吃喝玩乐,做不如法事情的朋友?
- 如瑞法师:每个人的福报都是自己修来的
- 本源法师: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要保持一定的距离
- 济群法师:佛教对世界的认识——因缘因果
- 如瑞法师:护念他人善用心,学佛慈悲须践行
- 本源法师:如何报答佛陀的恩德?依教奉行就是对佛最好的报恩
- 济群法师:真正完美的人生,需要具足这八种圆满
- 本源法师:只有无漏的福德,才是真正的功德
- 如瑞法师:印光大师是后世佛弟子学习的榜样
- 理海法师:无论哪种供养,都离不开善用一颗欢喜的心
- [生活故事]也就只是像那么回事
- [佛与人生]妨碍善行,损耗钱财的六种过失,在家佛教徒要防范
- [汉传人物问答]学佛最终只是让自己和众生解脱吗?
- [佛化家庭]世间的孝有几种,子女怎么做才是世间最圆满的孝道?
- [白云禅师]傲慢与偏见,学佛人要远诸傲慢,调整偏见
- [宗性法师]佛教说不能执著,是否意味着看淡甚至放弃努力理想?
- [佛与人生]放下过去,期待明天,对未来心存一份期望
- [佛学常识]四真道行是什么意思?佛说四圣谛的目的
- [人物故事]济公是真实存在的吗?济颠和尚的神奇传说
- [禅宗文化]灵隐寺在哪?杭州最早的佛教名刹灵隐寺介绍
- [黑茶]认识黑茶,黑茶的分类与营养功效
- [禅宗思想]禅宗的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”
- [广钦和尚]在家学佛,应如何做人?
- [宗门故事]无上大法难的不是解,而是真
- [普洱茶]小寒喝什么茶?普洱熟茶、黑茶、红茶
- [佛理禅机]知足不是得少为足
- [生活故事]因为有禅,所以有缘




